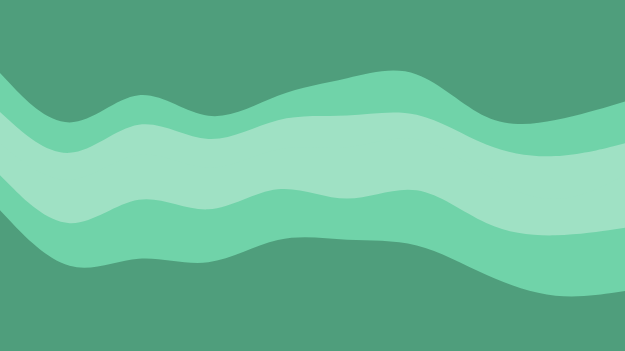鸳怨误
瞧那俊俏马,马上骑着人,满面风光样,人人见后言,贺喜贺喜,状元郎,我朝独一人。他下了马,边收着贺礼,边喝着他人递上的酒,欢欢笑笑的进他家那府中,旁人皆言,他家那府邸,怕是与那皇亲国戚差不了多少。
父见儿喜归,出门笑迎道:“后继有人,后继有人啊。”众人见后,大多皆跪下言道:“见过尚书大人。”其父见此,可谓是笑脸相迎,一个个边扶起边说:“少如此,少如此,如此,我与皇上还有何区别?谢过便好。”
宴上,一人笑言道:“状元如此大才,怎不在此宴上作诗一首?”众人听闻,净起哄道:“作一首!作一首!”他听闻后,不过多时,便言道:
九衢车马尘如雨,万井笙歌月满盘。
天上星辰环北极,人间风露湿衣冠。
众人听闻,高声呼道:“好!好!”此时一半疯不疯的瘸子杵着拐,正巧走过府门,边走边囔道:
窗前荒草乡,手可触天长。
身堕水中泣,幽幽府邸丧。
且真是
金银穿戴花,日夜寢衣乐。
一念又一思,无声咽水涩。
那送礼的众人见了他,有几人边赶边言道:“你这疯子,如今大喜的日子,净来这扫兴,走走走!”推搡中,那他倒了,刚想起身,便被一旁的官兵抓起。后来听闻,他饿死了。
本以为,他考上状元后将一步高升,可惜,他却是沉迷酒水,常常出入那曲中,街坊四邻皆以为,他是鬼附生了,不然怎如此?他父见此还找了好几个大师,做了几天几夜的法,还是无效。其父不解,便派人跟踪于他,跟至曲中后,那人本以为他会点几个貌美女子,不曾想竟是点了一男子,后来人评价此事时,说那男子的长相是
曲中难得外,彩鹢暮连翩。
蛮腰细袅袅,葳蕤更馀妍。
鼓楫乘神波,弄笑起云边。
惊澜翻鱼藻,含欣歌采莲。
丹唇何姣好,及此荷花鲜。
那男子至他身旁,边倒酒边言道:“先生近日多来曲中,不怕旁人说些闲话?”
他抚过他脸,轻言:“我与我夫处,旁人可说何许?”
其脸羞了羞而言道:“我何时应过?葫芦话倒是一车。”
他凑过去言道:“若我今日醉了,玩乐于你,会如何?”
其递过酒而言:“会如何?我本就做此的,你不嫌脏,任你。”
他言:“好,那我赎了你可好?”
其听闻且笑容现后凑过去而言:“好,真的嘛。”
他调戏道:“真的,但你要跟我过。”
其听而傲娇的说道:“我被玩死,都不和你过!”
他边招呼着老鸨边与其言道:“这可由不得你。”
其言:“啊?你父会同意?”
老鸨来后问询道:“客官有何吩咐,可是他做了什么惹了客官?”
他言:“未曾未曾,我是想言道,赎他需几两?”
老鸨言道:“不多不多,十五两足以。”
他听而对其笑言:“你可比少许字画还贵些啊。”
其对老鸨言:“老妈子,再多要点!”
老鸨对其言:“莫强了,如今有个好人家赎你,自足好。”
其言:“我可不跟他!”
老鸨听闻,则对他言:“其不听,若是赎了,不与你走,我怕是管不了。”
他言道:“我先回家取银,少许时候来赎其,莫要旁人碰与他。”
老鸨言道:“好了好了。”
他便离去,其见与老鸨言道:“老妈子,你就不可不要他赎我了?”
老鸨言:“这桩买卖还不好了?不可不可,你好生在此呆着。”
其听而一旁怨细言,老鸨未理。
他出曲中与家仆见,笑问道:“余父遣尔至乎?”
家仆笑指言:“言语文邹邹,我等难听言,所来跟踪,瞧你不做官,不娶妻,原是在曲中有缘。”
他笑言:“既知,待会可能帮我与父言说一二?”
家仆不言,便走。
至家中,几家仆见,闲语道:“今日怎回如此早?”
又闲语:“怕是又缺银。”
且闲语:“老爷不在,怎讨得?”
至家中,入主室,室中柜,皆翻遍,好几两,未曾够,闻讯人,皆不知,又翻寻,未曾够。
他母见而言:“找何物?”
他言道:“钱。”
他母上前阻而言:“翻了翻,乱一糟。”
他言道:“那你给我?”
他母言:“怎如此急躁?”
他言道:“不给就别说话!”
他母言:“好了好了,急着做什么?说了便给。”
他言道:“娶媳妇。”
他母言:“你整日风花雪月,还娶媳妇?糟蹋了人家?离去离去。”
他言道:“那我继续翻,一旁看着去。”
他母言:“好声好气,不听劝,你怎找得?翻吧翻吧。”言后离。
半时辰,他父回,他见言:“给钱。”
他父言:“日夜玩闹,不成样子,给个鬼。”
他言道:“给不给?”
他父言:“干嘛去?”
他言道:“娶媳妇。”
他父言:“你娶媳妇,不得给我看看?”
他言道:“给你看干嘛?得了得了,给钱。”
他父言:“主室床头下,有五两。”
他言道:“五两你就想娶媳妇?你娶我妈用五两娶的?不够。”
他父言:“要多少。”
他言道:“三十两。”
他父言:“什么媳妇?三十两,你脑子怎么了?啊?”
他言道:“给钱。”
他父言:“中堂牌匾里,应该,还有十三两。”
他言道:“翻过了,不够。”
他父言:“我要你乱翻了?”边言边追打。
他言道:“停,停,别打,差三两。”
他父言:“我给你个毛细。”
他言道:“给钱。”
他父掏了掏,抖了抖后言:“最后三两了,你要为父,怎办?”
他言道:“找我妈要。”
他父言:“你娶媳妇,她会同意个鬼,糟蹋人家,啧啧啧。”
他接过银离去而言:“啧什么啧。”
回曲中,牵其手,离曲中。
笑问其:“住何处?”
其言道:“牵我出来,住处都未曾有?”
他言道:“有有有,夫人请。”
其言道:“酸不酸啊。”
回至家,他父见,上前问:“不是去娶媳妇?媳妇呢?”
他牵其手笑言道:“不就在我旁?”
他父言:“你有病是吧,娶个男的?啊?”
他言道:“不行否?”
他父言:“出去出去!来人来人,赶出去。”
他言道:“好好好,走走走。”
他父言:“停,娶都娶了,为父啊,也不是啊,很封建啊,但啊,作为啊,交换,明天为父给你在朝中的安排,该去了。”
其言道:“那我呢?”
他父言:“你听他的啊?你问我?”
其言道:“我也想要个官……”
他父言:“放屁,你当朝廷的官是野草啊,遍地都是?”
他言道:“别凶他。”
他父言:“滚。”后离去。
其言道:“强取豪夺,哪有书生这么霸道的?”
他言道:“好了好了,抱抱。”
其言道:“抱你奶奶个腿,把我赎回来,就给你当压房夫人啊?我才不要。”
他言道:“那既然你不想……那你走喂。”
其言道:“好。”
他言道:“停,不过,你得去某个正经差事。”
其言道:“我回去卖身,用你管。”
他抱其后言:“闹什么?睡觉。”
床上:
他言道:“你说还有和人碰过你身?”
其言道:“那可多,我可脏,莫乱碰。”
他言道:“牛皮还挺大,笑话,你去曲中的第一天都是我点的你,日后我是天天去,还有人碰过?”
其言道:“得了,睡觉。”
来晨,被宣,至殿中。
上言道:“听闻爱卿前日才娶一妻,如今终于来朝,难见难见。”
他言道:“皇上笑话了,不知这早朝,我本不应参与,为何宣我,有何事?”
上言道:“尚书大人未与你言?”
他言道:“六部皆尚书,我怎知是哪位大人?”
上闻而指了指,笑了笑,他父插言:“皇上莫怪,昨日子刚娶妻,仓储之下,交代不多。”
上笑,一臣上奏:“黄河决堤。”一臣言:“城中灾民过千。”
上笑言:“户部照常批款便好,散朝。”
他问父:“这一早朝,我连我是什么官都不知。”
父言:“噢,户部侍郎,在我手下干活。”
他言:“批款怎批,我看这账上,不过三十万两。”
父言:“亏空,盐税收补,先批下去。”
他言:“黄河决堤,八十万两,赈济受灾官府五十万两,一百三十万两的亏空,怎补?”
父言:“为父做事,一边去。”
他言:“既叫我来,又叫我走,何意?”
父言:“行,我这便去上那,请上给你我这个户部尚书。”
他言:“行。”
上批,父归,他升。
父笑问:“大尚书?怎补?你爹我回乡下养老。”
他未言,书奏:
户部亏空,灾民苦楚,上百县遭淹,愿上念民苦,调拨内务银两。
后回家中,其见言:“舍得回了?”
他言:“累了一日,却得讥讽。”
其言:“做何了?无非是处户部椅上悠闲乐。”
他言:“我还写了几奏。”
其言:“那几奏,动了?”
他言:“额……”
监来宣:“上宣尔至。”
他对其言:“少许时见。”
其言:“假忙活。”
宫中书房内:
上边书边言:“这批款,朕怎听闻,还未批下?”
他言道:“皇上,臣定当加急而办。”
上言道:“限今日,灾民要救,黄河要治,匈奴近日朕闻,行军逼近多。”
他言:“臣知,臣退。”
至工部:
工部尚书见,面笑欢喜言:“尚书大人,来从何事?”
他言道:“与你商一事。”
工部尚书闻而言:“何事何事?坐否?”
他坐后言:“工部目前支出八百九十二万两,年底商谈时,你支出六部之首啊。”
工部尚书笑言:“尚书大人,您刚上来有所不知,就说今年,先是皇上要修宫殿,又是要建堤坝,这每一笔都不能少啊。”
他笑言:“尚书大人,这既有建堤坝的款,这款是建哪条?”
工部尚书喝了喝茶后说:“江南,你也不是不知,那地方若是洪涝,不知又要损失多少。”
他想了想后说:“要不这样,江南那的建堤坝,移来先治黄河和灾民。”
工部尚书无所谓的说:“那随便你咯,到时候皇上要杀人别带上我。”
他听后又说:“尚书大人这话说的,既然江南不能移,那你说如何。”
工部尚书说:“钱在你哪,和我有关?”
他言:“行,你现在进宫跟皇上交代。”
工部尚书说:“交代什么?户部没钱,找我开刷?”
他又笑言:“没找你开刷,这不是在商量办法嘛。”
工部尚书言:“其它四部,怎么不去找?”
他笑言道:“北方要打仗,你我要工资,哪来的钱?”
工部尚书言:“你别跟我扯皮,你是户部尚书,还是我是?”
他笑言:“好好好,一毛不拔?”
工部尚书言:“拔,有事别拉着我。”
他言:“好好好。”后离去。
至家中,其见问:“酉时了,天都昏了,瞎忙,娶我回此就如此晾着?”
他扶其言道:“朝中没钱,为这事我倒是想破了头皮了,竟还这般数落我。”
其听言:“哼。”
他捏其脸言:“别不开心,不如陪我上朝?”
其言:“上能同意?再说了,哪有带家属的先例?”
他笑言:“你不是会写文章?灾后上应该会开恩科。”
其言:“中不了的。”
他言:“怎会呢?你这么厉害。”
其言道:“好了好了,吃饭睡觉,这么晚回来,菜都凉了,我热热。”
至饭桌,他吃了几口,后说道:“天啊,难吃。”
其言道:“你还嫌弃上了?别吃了!”
他言道:“你看,这都糊了。”
其言:“饿着吧!”
他言道:“额……可真的难吃……”
其言道:“噢。”
他言道:“我好奇你吃什么?”
其言:“糕点。”
他言道:“也分我一块。”
其言:“不行。”
他言道:“为何?”
其言:“吃你的饭去。”
他至其旁,先是扶至他身言:“故意整我?”
其言:“没有……”趁其不注意,抢过几块,其反应过来后言道:“不要脸,强我东西,哪有你这么不要脸的?”
他边吃边言:“要你不给我。”
其言:“你慢慢吃吧,我睡觉去,欺负人……”
他言道:“略略略。”
来晨-朝中:
上言道:“这灾民和黄河如何了?”
他出众臣队后言道:“灾款批下去了。”
内阁首辅突言道:“是,并且京城的灾民基本都安置好了。”他见这架势,便退回众臣队。
内阁首辅又言道:“皇上,如今虽是灾事之多,但也有好事,就例如本朝与南洋诸国刚谈成五千引茶的生意,预计可带来数百万两白银。”
上摆摆手笑而言道:“南洋邦国,皆伊小国。”
内阁首辅言:“皇上说的是,此次贸易由民间商人所替,官府抽成九成。”
上言道:“如此便好。”
内阁次辅言:“皇上,这五千引茶,怕是三千引都卖不出。”
上言:“为何?”
内阁首辅抢言道:“皇上,卖得出,南方各地众居民早已种起茶叶,差价也起码有九成之多。”
内阁次辅言:“皇上,若按首辅大人所言,南方各地,所种粮少,北方各地难以补得。”
上言:“民生也许关照,如今太平盛世,定要使百姓安居。”
他言:“今各部开支甚多,伤及国本。”
内阁首辅缓言:“等茶卖出,便补上了。”
内阁大臣兼户部侍郎甲言:“臣以为,户部亏空,不单因各部开支,且因税收的减少,据统计,甲子年至庚午年期间,税收每年减少基本在五十万两到二十万两之间活动,特别是盐税,从甲子年启每年减少有八到十三万两,就比如去年,在没什么灾的情况下,盐税只有不到二百万两。”
内阁首辅言:“虽说去年未有什么大灾,可南方各省所记田地农户共减少多达二十五万户。”
上言:“朕知,散朝。”
散朝后他被上宣至宫中。
上言:“今国库缺钱你也是知道的。”
他言:“皇上,亏空只是暂时的,明年便可补上。”
上言:“你莫幌我,刚刚朝上你也听了,今年江南各省的盐税你与乙丙二人去收。”
他言:“臣以为,不妥,臣还兼着尚书一职,怎能随意离京?”
上言:“甲替你当着先便可。”
他言:“臣遵旨……”后退去。
至吏部:
他见吏部尚书,便闻讯到:“这乙,丙两人,今日皇上提起,我初来乍到,还不知,不知尚书大人可有档案?”
吏部尚书笑言:“这内阁的阁老都还未曾认全?”
他笑言:“刚来两三日,朝中人多,难能认全。”
吏部尚书言:“那二人,乙兼任吏部侍郎,之前应该是在南边任过父母官,且拜在首辅大人门下。而那丙兼任通政使,同样是从地方升上来的,当时是次辅举荐的。”
他言:“多谢尚书大人所言,晚辈谢过。”
吏部尚书言:“莫谢,莫谢,你父曾经也多相助于我。”
他笑言:“如今,你我二部还需帮衬啊。”
吏部尚书言:“是也。”
闲聊几句后离去。
至家中:
他未见其,问仆其去何处?
仆言:“今早便出了,我也不知。”
他闻言:“你不看着些许他?”
仆言:“他未曾要我跟去。”
他闻非言后至书房。
其处:
在街中逛,至那茶馆中,本仅喝喝茶,后又至台中,唱起插曲道:
凌寒恶风气密,岭间凄微雨。伤人绪、抚过空空,笑问身侧人语。花草应、凄洏了却,惓惓致得卬欹苦。念思南北各东西,曷可亲处?
冬离风停,处树痕下,等闲常在如。暄风及、鸟雀呼晴,水塘荷花接露,夜凉明月温酒,甚悆,惜乏其,鱼伤绪,曷鱼堪依女,瞳长天青云雾。
阴晴难定,风啸后辞,声声如棉雨,心窍细、甚欲先汝。言语颇多,难表鱼心。若于鱼侮,荒山坟冢,飘飘絮白,黄泉路上非知命,
思情些许、乏声消沮。言中语,尽汇一言,上文皆言,可尔欲鱼否?
暄风又起,草色天涯,脉脉牵携女,看着皓月升空宇,潸淚平容。
人死丧丧,黄泉路去。阴间且会,前生情债,一生难復,需数世。欠卿多、死后尸魂侣。幽幽府邸,红床鸳色被中,寢衣翻趣。【莺啼序·无题·词林正韵】
有人跟曲道:
白絮飘,婿气飘,阴使钩其丧状憔,其前沮丧熬。
乐寥寥,空寥寥,涕泣无声秋雨娇,至幽于女瞧。【长相思·无题·新韵】
有人又跟道:
夏过三瞳白藏,落花满地成堆。小楼独自倚徘徊。望断天涯孤鬼。
燕子归来何处,杜鹃啼破深杯。夕阳西下水东回。肠断寂悲笑意。【西江月·无题·词林正韵】
台下皆叫好,茶馆递来酒,一饮千愁散。
暂收